互聯網新聞信息許可證服務編號:61120190002
陜西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029-63907152
2025-02-25 14:31:15 來源:陽光網-陽光報
分享到

大美西部觀察往期發文精選已結集出版《大美西部觀察文集》。
城鄉文明建設的時代主題
——評長篇小說《回家》的價值走向
常智奇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歷史時期。我們的文學要在一時代的變革中,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及時地記錄人民群眾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先進經驗,提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深入思考的問題。王海的長篇小說《回家》,正是在這一點上應合了偉大時代的重大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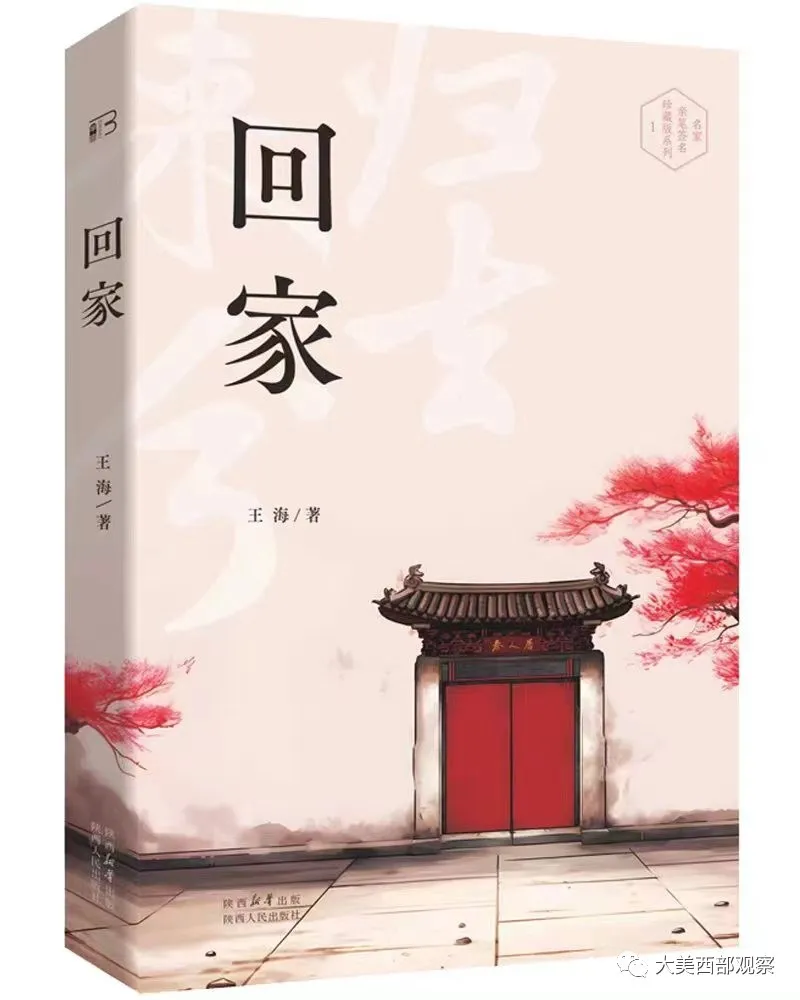
作者聲稱 《回家》是他“農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天堂》《城市門》《回家》)。可見,他對這部作品付出辛勤勞作的珍重,以及寄寓的思想感情的深切。《回家》以古城咸陽為敘事空間,聚焦失地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生存困境、精神漂泊,表現精神“回家”的熱切期盼。這部作品不僅延續了作者對“三農”問題的深切關注,更以文學化的視角揭示了現代性沖擊下農耕文明與城市文明的碰撞、傳統倫理的裂變與重構,以及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精神救贖之路。
一、雙向“回家”的悖論與超越
人性的二重性,道德的二重性,資本創造文明的二重性,決定了農耕文明在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的精神歸家的二重性。“回家”在小說《回家》的敘事中具有雙重象征意義:倫理空間與價值空間,物理空間與精神空間,雙向歸家重建的意義。這一主題貫穿全書,既有對現實生存窘迫的真實記錄,也有對現代精神焦慮的理想期盼;既是對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生存困境的回應,也是對中華文化傳統中“安土重遷”情結的現代性反思。
物理意義的回家
失根者的生存悖論。城市化浪潮吞噬了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小說中的豆花、李奇、子衿等人物,被迫離開祖輩生活的五陵原,成為“無根”的都市漂泊者。他們雖在物質層面通過創業(如豆花創辦“秦人居”旅館、豆丫成立“新市民服務中心”)實現了經濟獨立,但精神上始終困頓于“家”的失落感。子衿的“入土為安”執念尤為典型:他晚年歸鄉,拒絕現代樓房,執意于田間筑屋、保存糧種,甚至要求死后棺木中放置種子,這種近乎偏執的行為,正是對土地依存感的極致表達。王海通過這一人物,揭示了農耕文明基因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頑強存續,以及其與城市文明的深層沖突。
精神意義的回家
倫理重構與文化尋根。小說中的“回家”更指向一種精神歸宿的追尋。豆花與李奇的破鏡重圓、豆丫對傳統家庭倫理的堅守,乃至老王妻子卓花回歸四川原生家庭的選擇,均體現了作者對傳統家庭價值的隱性肯定。這種回歸并非簡單的保守主義回潮,而是對現代性情感異化(如丁克家庭、不婚主義)的反思性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豆丫成立的“新市民服務中心”,通過技能培訓、法律咨詢和互助社群,為失地農民在都市中重建了一個“類鄉土”的精神共同體,既延續了農耕文明的互助傳統,又注入了現代公民社會的組織理念,成為“回家”主題的創造性升華。小說通過進城農民對“家”的復雜情感,揭示了城市化進程中傳統家庭關系的瓦解與重建。例如,卓花與“隔壁老王”的婚姻矛盾,以及她最終選擇回到四川老家的情節,既反映了城市化背景下家庭紐帶的脆弱性,也體現了傳統倫理中“根”的不可替代性。王蒙指出,卓花的返鄉行為“充滿中華文化傳統”,是對安土重遷、慎終追遠等倫理價值的回歸。
許得他爸出獄后執意回歸農村老屋的執念,進一步凸顯了傳統倫理中“落葉歸根”的道德訴求,盡管這種回歸被現代文明視為“保守”,卻映射出城市化進程中個體對精神歸屬的強烈渴望。
道德的困境與現代性的反思
“隔壁老王”的荒誕行為(如策劃“英雄救美”以接近豆花),展現了城市化背景下傳統道德觀念的異化。他的失敗既是對功利主義價值觀的諷刺,也暗示了倫理失序的代價。王海通過這一角色,揭示了農民在身份轉化過程中面臨的道德迷失與救贖需求。
二、鄉土意識與現代性的沖突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城市化建設的新時代,表現土地與人的家國情懷,是偉大時代的嚴峻命題,《回家》在表現這一偉大命題的過程當中,表現出以下的特點:
倫理與價值的互文性
《回家》通過“家”的意象建構和組合方式,將道德判斷與價值判斷交織為“雙向回歸”的敘事結構。例如,豆丫在城市創業成功后仍選擇返鄉,既是對家庭責任的倫理回應,也是對鄉土文化價值的重新認定。這種回歸超越了簡單的城鄉對立,指向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融合的可能性。具體的講有以下幾點:
歷史與當下的對話
作者以咸陽原上的農民為縮影,通過“農村三部曲”完整呈現了中國農民從“分地”“失地”到“尋家”的歷史軌跡。小說將鄉土意識根植于中國農民的血路之中,用歷史意識壓模農民的鄉土意識,用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的雙重審視,冷峻地分析我們這個民族在城市化建設中,民族精神在歸家途中,繼承與發展的雙向關系。這種創作視角既是對傳統倫理的繼承,也是對現代化進程中價值斷裂的修補。
城市化代價的倫理拷問
小說直指失地農民為城市繁榮付出的生命代價,如作者所言,“他們以土地和生命為代價換取了城市的豪情”。 這可能是我們這個民族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應該付出的歷史性的代價。問題是我們的文學要對我們這個民族付出這一歷史性的代價中的價值和意義給予充分的肯定。這種批判性地敘事不能僅僅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中的問題的揭露,更應該是對發展倫理的深刻反思。
人文精神的終極回歸
海德格爾認為:“人生充滿勞績,但仍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怎樣才是詩意的棲居?有人認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是詩意的棲居,有人認為“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是詩意的棲居,有人認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辟天下寒士盡歡顏”是詩意的棲居,有人認為“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 是詩意的棲居……《回家》更多的在詩人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基座上,表現中國精神的鄉土頌。作品通過農民“整建家園的努力”與“頑強的生命力”,傳遞出對人性尊嚴與道德理想的堅守。這種回歸既是倫理的,也是價值的,既有現實的真實記錄,也有終極的精神追尋。
《回家》的“雙向回歸”思想,既是對城市化進程中倫理失序的批判,也是對傳統價值的創造性轉化。作品通過咸陽農民的故事,構建了一個關于“家”的哲學命題:在現代化進程中,唯有在倫理與價值的動態平衡中尋找回歸路徑,才能實現個體與社會的共同救贖。
三、為時代的普通人物立傳
表現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普通勞動者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恩怨情仇,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使命和神圣天職。《回家》以平民視角刻畫了數十位“小人物”,他們雖無顯赫身份,卻在命運的跌宕中折射出城鄉轉型的集體陣痛。它的價值和意義在于:
女性角色的突圍與困頓
豆花與豆丫作為核心女性形象,展現了失地農民中女性的雙重境遇。豆花從離婚后經營旅館到最終與李奇復合,其情感軌跡暗含對傳統家庭倫理的妥協與回歸;豆丫則更具現代性色彩,她以保潔公司創業者的身份突破性別桎梏,卻在婚姻破裂后陷入情感孤島。兩人的命運對比,揭示了城市化進程中女性既要承擔經濟獨立壓力,又難以擺脫傳統倫理束縛的復雜處境。而豆丫的“新市民服務中心”,則象征了女性作為社會聯結者的能動性,將鄉土互助精神轉化為現代社群建設的資源。
男性角色的失語與異化
得福、老王、許得等男性角色,則呈現了更為撕裂的精神圖景。得福的“守身如玉”與終身未娶,既是傳統道德觀的堅守,也是城市化進程中底層男性經濟弱勢的悲劇縮影;老王的花心與投機,反映了小市民在都市生存中的道德潰散;許得的“花花公子”形象,則隱喻了消費主義對鄉土倫理的解構。這些人物共同構成了一幅男性氣質在城鄉夾縫中逐漸異化的眾生相。
代際沖突的文化傳承
子衿與兒子姬天的代際矛盾,濃縮了傳統與現代的價值沖突。子衿對土地與種子的執念,與姬天對現代商業邏輯的接納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姬天最終繼承父親衣缽、回歸鄉土事業,暗示了傳統文化基因在代際更迭中的隱性延續。
四、地理性的敘事與精神性的寓言
成功的作品往往是在地理性的敘事中寓于精神性的寄托。回家是在地理性的敘事中,寄托著表現民族精神回家的精神情懷。作品的敘事風格兼有現實主義底色與象征主義深度,形成獨特的“咸陽敘事”風格。
地理空間的文學賦形
小說以咸陽湖、五陵原等真實地理空間為背景,通過方言俚語(如“隔壁兒老王”)、民俗細節(如石碾盤、皂角樹)的鋪陳,構建了一個充滿秦地風情的“文學咸陽”。這種地域性書寫不僅增強了文本的紀實感,更將城市化議題置于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中,避免了概念化表達。
二律背反的結構張力
作品采用“離鄉—歸鄉”的雙線敘事:一方面,失地農民在都市中掙扎求生;另一方面,成功者(如李奇)與失敗者(如陳進財)最終均踏上“回家”之路。這種結構暗合中國傳統文學中“出走—回歸”的母題,卻賦予其現代性內涵——無論是物理返鄉還是精神尋根,“回家”始終是一個未完成的動態過程
細節中的時代隱喻
小說中多處細節具有寓言色彩:子衿棺木中的種子象征農耕文明的永生渴望;豆丫的“新市民服務中心”則預示了鄉土倫理的現代轉化。王海通過微觀敘事,將個體命運升華為時代寓言,實現了“小故事”與“大歷史”的辯證統一。
五、城鄉巨變中的文學境鑒
文學總是要給人以審美的感受,開悟人的思想,啟發人對現實與理想的生存思考,引領人走出迷茫和困惑,為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努力。《回家》立足于現實生活的真實性,努力表現人對美好生活期盼的超越性在于,它不僅是農民命運的白描,更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刻反思。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對城鎮化代價的文學警示
我們正在從事著一項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偉大的社會實踐。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活動,充滿了探索性和實驗性。小說通過拆遷、土地閑置、農民進城等情節,揭示了城鎮化進程中“家園喪失”的集體創傷。得福“攢不夠彩禮”的吶喊,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千百萬農村青年生存困境的縮影。作者以文學之筆,叩問了“如何安置失地農民”這一緊迫的社會命題。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也是《回家》作品對城市化代價的文學警示。
傳統文化向現代轉化的可能性
豆丫的“新市民服務中心”與子衿的糧種保存行動,分別從社會組織與生態倫理的角度,探索了農耕文明基因融入現代生活的路徑。這種嘗試既非懷舊式的文化保守主義,亦非對現代性的全盤接納,而是試圖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尋找平衡點
文學對歷史記憶的銘刻
《回家》以文學形式記錄了城市化進程中“被遺忘的群體”。 文學是民族精神記錄的秘史。表現民族精神在城鄉巨變中的作用、價值和意義,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核心價值觀。《回家》具有這種為農樹碑立傳史志價值。這種書寫不僅是對個體命運的關注,更是對時代集體記憶的搶救性保存。
總之,這是一部有時代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小說。它既直面了城市化帶來的精神陣痛,又未陷入簡單的批判或頌揚,而是以冷峻的筆觸揭示了“失根”的必然性,又以溫情的目光捕捉到“尋根”的可能性。小說結尾,無論是豆花的四合院團圓,還是子衿的“入土為安”,抑或豆丫的服務中心,均暗示了一種彌合城鄉裂痕的文化方案——在傳統倫理中注入現代性活力,在個體漂泊中重建共同體認同。這種“回家”,既是地理意義上的返鄉,更是文化基因的復蘇與精神家園的重構。在這個意義上,《回家》不僅是一部農民命運史,更是一曲獻給所有現代人的精神安魂曲。
2025年2月11日
于唐都古城大明宮遺址公園
作者簡介
常智奇,研究員、文學碩士、文藝評論家,陜西省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陜西省國學研究會副主席。曾任陜西省文學院院長、《延河》雜志主編。

△作者 常智奇